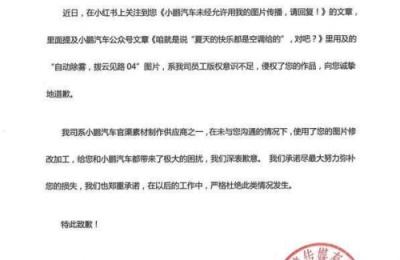孙文波(孙文波诗人)
孙文波,1956年出生,四川成都人。1985年开始诗歌写作,1986年起在国内外多种刊物发表作品。1990年以后亦开始诗歌批评的写作。作品被收入《后朦胧诗全集》《中国二十世纪新诗大典》《百年诗选》等多种选本。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瑞典语。曾参与主编《中国诗歌评论》《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主编《当代诗》。讫今已出版《地图上的旅行》(1997)、《给小蓓的俪歌》(1998)、《孙文波的诗》(2001)、《与无关有关》(2011)、《新山水诗》(2012)等八部诗集,以及文论集《在相对性中写作》(2010),随笔集《洞背笔记》(2019)。
洞背纪事(十四首)
奢侈诗
没有比蓄意让我更厌倦的。突兀,
也不惊奇。穿过墓园的十来分钟时间,
我阅读了好几座碑铭:陈氏伉俪,
乔姓考妣,还有一位张姓慈母。他们代表了
来世。对于我不过是过眼烟云。
我的目的是到海边栈道闲走,那里的曲折有意思。
人性的亭阁指向风景。是冬天
晒太阳的好去处。水面万金闪烁,有绝对性。
自然对应匠心。可以成为下午分析的本体。
的确如此。我或者凭栏远眺,
或者低头凝视。胸中有再造的蓝图。我知道这是
我的自以为是。小人物,也要以我为主、思想中心。
攀登栈道的顶部时,我已在世界上
划了一个圆,向四周弧射而去。
犹如史蒂文斯的瓮。当然并不指向未来。
在这里,我其实关心的是下午四点半钟。按照想象,
我应该到达奥特莱斯的星巴克,
咖啡的温润中放松身体。我把这看作晚年的奢侈。
它是一种理想。贫穷中谈论奢侈是奢侈的。
我容许自己奢侈,把这看作我生活的形而上学。
正是它使我远离人群也能独乐;
我一路研究了一块礁石。几只囚池的海豚。
也在太阳落下水面时,琢磨了它的壮丽。
沧然诗
突然响起的声音,惊吓登山者,
轰轰,或隆隆,不知从哪一片密林
传出,引得她们停下脚步,
张目四望,觉得每一棵树后都可能
藏着一只不知名的怪兽,或者
每一块怪石可能就是怪兽。使她们匆匆
结束一次无目的的攀登,心揣疑惑返回。
向我讲述时,仍一脸惊惧的表情。
十几天后,我登上她们走过的小道,攀登中,
被静谧吸引——真是好风景。
越是向上树林越是幽深,视野越是辽阔。
阳光的照耀下,巨大的岩石长坡
完全就像温暖的坐席。我坐下来后,
甚至产生不想离开的念头;眺望,如此幽远,
天地,只我独享。进入我耳朵的是旷古
就有的风摇晃草木的声音。
如此声音犹如一道屏幛,隔开我和世界。
直到淡岚之气从周遭慢慢向我围来。
让我念天地幽幽;幽幽,不思来者。
论异诗
……春节,犹如思想的加速器。
头脑里的场景大铺开——叠屋架梁。
还有人,逝者与活人,面目重复。
不过,我要描绘的是一个乡镇:华岳庙街。
干打垒照壁。土灶茶馆。黑棉袄黑裤。
粉丝包子。纸灯笼。每个人的童年都是梦幻的。
反梦幻的是社会。我的摇摇晃晃的
老祖父、老祖母;他们已是另一层空间的神。
我的神。他们正在天上游弋。
剩下我还在寻找旧的物事;老屋神龛下面的涂鸦,
两只山羊的尖角风化后的残片。
空间距离演变成数学。复杂的计算,
让我揣度超越的普遍性。以及人改造自然
带来的丧失;不对等,已经让我不能把过去与现在
重合在一起。消失带来无意义。
就像一幕皮影。时间给予的幻觉与量子漂移相似,
譬如一恍神窗外浮现的脸,
我必须定下心揣摸,是不是能够伸手抓住它?
就像饥饿的蟒蛇抓住大象。有多少妄想就生出
多少奇迹。如果我说,我可以
一步跨过岭南,再一步跨过秦岭。这是真的
——在我的身体里有一群大雁,几只鹰隼。
——在我的身体里有十架飞机,几颗卫星。
示 儿
……(广阔的)黑暗之上,你在飞。
我的思想也跟着你飞(洞背,已经深眠)。
越过国家的分界线。此去,都叫关山。
万里,只留下概念。我的头脑里,依次出现的是
蒙古、俄罗斯、德国与荷兰。变幻颜色的图册
标示的地名(让我小心分辨)。
同时,我还在分辨星象,猎户星座、长庚星。以及可能
出现的慧星。它划过天际燃烧的光芒,也许照亮了
你飞的右边(左边,世界在沉睡)。我希望
你能够透过舷窗看见,扑面而来的不仅是人类的 灯火,
还有城市的善(阿姆斯特丹、哥廷根的善,
华沙的善)。它们接纳你,犹如接纳一朵干渴的花。 而我,
则在继续的思想中,进入到自己的暮年
(仍然动荡的暮年)。就像此刻。我的身边欲望的 爆竹
响个不停(犹如枪声)。我还得用心
应对继续贫穷的理念,将之像年年有鱼(余)一样 守护。
对于我,它既是生之局促,也是骄傲的源泉。我希望
这也是你的骄傲。我思想着,当你终于
熬过漫长的行程。平安地降落在自己跋涉的目的地。
一切很灿烂;道路灿烂,房屋灿烂,人心灿烂。
如此,我就会看见,一抹朝霞已爬上我的窗沿。
眩晕叙
……强烈的反光,使大海变得眩目,
犹如一首诗的开始。接下来会发生
什么——一场激烈的海战,
一次隆重的围捕?——都不是这一片海域
曾经发生过的。只是想象——我仍然要说,
渴望看到不平凡的事情发生是
我的心理——如果突然地,
在我的眼睛里出现成千上万艘帆船冲撞在一起,
火光烧红了水,成群瓜头鲸、虎鲸、逆戟鲸
愤怒地跳跃——这样的戏剧性
会带来什么——历史,拐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坚定虚构再造一切的信心?
——那么,我会说,当一切平静以后,是不是能
看到沉船从海底升起,继续它的航程。
它携带的神秘终将抵达我的笔端。
它成为纽带,紧紧嵌刻在文字中
——或许这还是太复杂。实际上随着一片云遮挡,
眩目的光线消失。映入我眼里的大海,
灰暗如揉皱的报纸——我发现,如果我愿意,
将从中读出一句告诫:大海太深邃了。
它带来的神秘永远层出不穷——要写好它,
我不过是摇着一条小舢舨在海中捞捕……
答问叙
与我同行的人已经停步,有的
躺在词语中,有的干脆转向了金融。
只有我还在未知中,寻找未知。
其实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一大群麒麟,
或者一只骆驼?我知道的只是必须走。
有时候,我觉得已经走到绝望中,
有时候,又觉得好像已经攀援理想的高峰。
不断的虚妄,不断地注入我的内心。
让我感觉累和虚荣。想一想则是,
只有虚荣才能带来前进的动力。
只有妄想,才会让我觉得能够攀上命运的巅峰。
如果有人要问,这样的人生,有何欢乐。
我的回答是,以苦为乐。我要说的是,
苦乐的转换,不过是一种认识,一种哲学。
这一点,犹如有的人,喜欢吃肉,
有的人,喜欢吃素。有的人,喜欢宅居,
有的人,喜欢路上奔波。一切,都是选择。
正确的选择,未必有正确结果。错误的
选择,用正确的心态承受。正是如此,
我觉得在路上,必须永远。必须长久。
乡村巴士纪事
我坐在乡村巴士上一路沿着海边走;
十七英里、玫瑰海岸、上洞村、土洋,
还经过了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每到一站都有上来的旅客;车越挤越满。
一个中年男人,不知为什么一上车
就骂骂咧咧(他说的粤语我一句没有听懂)。
我的注意力一边在海一边在人。车的移动中
海一成不变,仍然是深蓝在
阳光中轻颤。有几分钟,我能看到一艘大船
一动不动仿佛停在海里,看上去如静物画。
奇异。我心里嘀咕。想到有人写过坐乡村巴士;
一座热带岛屿,同车的黑皮肤少女,提篮子的
瘸腿老妇。他遗落香烟有人捡到又还给他。
他在飞舞的尘土中感到世界美好并
流下眼泪。我的巴士在没有尘土的沥青路行驶
是另一种景象;有时沿山上坡、下坡,急转弯。
车上的人都沉默不语(除了骂骂咧咧
那人和电脑机械的报站声)。只是低头玩手机。
没有玩手机的,两眼木然盯着窗外景色
(少女、妇人、小伙全如此)。我就此感到
坐在同一辆车上,我和他们就像有墙隔绝;
他们让我突然觉得坐车是非常孤独的事
——巴士的摇晃中,我的孤独有如大海。
戊戌年七月初二溪涌沙滩随手记
嘿嗬……雨后的海水浑浊。沙滩上
冲上来不少脏东西;塑料袋,枯树枝,
藻叶,一只破球鞋,几条小死鱼。
除此沙滩上还有十几个人,男女各一半。
他们大多在用手机拍照,只有一个人
蹲着玩沙子。这时候,我就像一个观察者,
坐在堤岸边的长椅上打量他们。
同时,打量着空旷的海。它的确非常空旷。
望着它,我的脑袋里突然想到
这几天读到的新闻;离岸流卷走一对双胞胎。
逆戟鲸带着死亡的幼仔狂奔一千多英里。
都是特别悲伤的事情。想着想着,
我一下子觉得,眼前的海变得陌生、神秘。
“熟悉的,并不熟悉”,“大海犹如世界剧场”。
我的脑袋里冒出这样的句子。
它们让我觉得我此刻看到的一切,尽管平静,
不过是序曲或幕间休息。只是我并不知道,
什么时候它会上演大戏——就像兰波的
《醉舟》描写的那样。就在我这样想时,
从远处的海岬,拐出了一艘红色的货轮。
瓶中芦苇
红色芦苇,一簇,插入花瓶。
点缀了桌子——转着圈,你欣赏。
没有注意它在褪色。发现,
是第二天早晨的事——它已经浅灰。
很奇怪不是?不过,仍然好看。
更楚楚动人。这是干枯的过程?
可能如此——思想芦苇。这是谁说的?
钻进你的大脑。帕斯卡尔,
或者庄子。红到灰,内在的变化轨迹,
无从窥视只能猜测。生命的汁液
从有到无。消失静静地发生。真是神秘。
这就是离开,就是自然的意志?——
你要生出悲悯心,自责自己的行为吗?
当它长在山上,它是自然之子。
现在不是了——玩物。人自恋的牺牲品
——无线上纲:自然美让位人工美。
悲乎?不能深究。深究。只剩下
谴责——不如定格。转瞬即失也是意义,
使你努力回忆它的昨天,柔荑、绰约,
好像是少女——不过,你仍然相信
它还在思想。它思想的内容:拒绝。
诗的结构
——溪涌海岸、洞背村,一所学校
和一幢楼,开放的空间和封闭的环境,
沉思在其中的利弊,已经显现出来。
外界喧嚣不为所动。无论轻松过关到红磡,
还是进城到万象天地和欢乐海岸,
都不能代替你呆在此处,目睹日升月落。
你已经习惯每个下午沿绿道登山,
站在崖边眺海,对面起伏的山峦,如水墨。
而头脑中则完全是另外的景象,
取决阅读的书,昨天是晚唐的混乱,今天是
爱尔兰或加勒比海。激荡风云在心中翻滚。
如何谈论?可能是关于天气的一次记述,
可能是从书中获得的材料的整理。
哪怕其中谈到了季节,植物生长和凋零;
金盏花、桃金娘和石斑木,来自想象的营造。
具体描写并不具体,是臆想和领悟。
其中很多细节:某个傍晚被花吸引,不顾扎手
折下一枝,或者突然出现的爆炸事件点燃
游行队伍。这些意味什么?是大脑非常活跃。
身在一处固定的地方,重复度日,
如果没有想象,相当无味。而写作是纵横术,
天经地纬,东南西北,需要的是不拘一格。
对贫乏的超越。有些甚至是臆造。就像只是
一个闪现的念头,历史就被迅速穿越。
分明中,犹如驭云术,从空无中寻找实有。
落实下来,也许是对李商隐的沉思,也许是
看到欧洲的一条街上,某某某正在散步。
重回洞背纪事
支撑我的现在的是两个支架,
它们隐藏在身体内最核心的部位。
我知道这事实。但是没有感觉。
我仍然一天走动一万步,在街道乱逛。
打望的眼睛停留在年轻女人的身上,
色情想象还在泛起。这是永恒的
猥琐。那些为老不尊的说辞,可以安放
在我的身上。是的,臆造的返回,
我每天都在设计,一个二十岁的青年
正在成长,新生的荷尔蒙窜如竹笋。
有什么不行的呢?只要有药,那些延迟的
衰老就是可能。我每日定时吞食它们。
相互的角力。以至于就在前两天,
我又开始驾车千里狂奔。一路上望着山峦
从眼前快速闪过,仍然是征服。
不是“千里江陵一日还”,而是从西向东,
不断地跨越直到海边。没有被身体背叛。
现在,当我安静地坐在自己的桌前,
打开电脑。思绪仍然如沸腾。我知道
我还有无数诗篇要写就。从此以后,
我写下的所有文字都是与衰老抗争。
三月二十六日的蝴蝶梦
蝴蝶已飞舞了很多个世纪,如今还在
空中飞舞——谁凝视它,谁就成为了它。
这是我读到的无数故事。这只怪异的
蝴蝶令我迷惑,有时候是恐惧,它在人的
灵魂中的飞舞,变成了对世界的理解,
好像特别玄乎。让我思想,当人们用蝴蝶的
眼睛看世界,到底能看到什么?
能看到一座城的变化?从无中涌出的众多事物,
如今已改变世界的模样。它能够怎样
飞舞在这些事物中间;譬如它飞舞在摩天大楼的
玻璃幕墙前,或者飞舞在路上飞驶的汽车前;
慢一步,它的身体将撞碎在挡风玻璃上。
如果它感到不理解这个世界,又能做出什么?
我想象不出人们说的它之梦。有什么可梦?
越来越少的山林,草木,让它难以获得吮吸花蕊
的乐趣。所谓的逍遥,根本成为了臆想。
使我不得不相信,蝴蝶,肯定仅仅想成为蝴蝶,
而不是人的灵魂进入其中。首先我就
不想成为蝴蝶。尽管有时候,看到它的飞舞
姿态翩翩。我仍然不想。这种不想,说明了
什么?说明的是,我只用我的眼睛看世界,
我只能在我的现实中成为我而不是另一个。
永无止境
书越读越多。从小学课本,用了九年
你到达一篇文章赏析。它告诉你它的来源
在于一本古书,在那里,圣人论说天下。
把道理引向几本书。正是这几本书,繁衍出
更多的书。总有人在书中谈论书。还有人
从书中发现了新的书。追踪似阅读,让你从
一本书到达另一本书,从另一本书中
发现新的书。它使你翻开一本,另外的就在旁边
等着你;变成了一生二,二生三。
阅读变成永无止境的事情。让你发现,书不是
越读越少,是越读越多。如果比喻,它就是一条河,
越来越长,分岔的支流越来越多,它就是山,
不是一座山,而是群峰连绵,翻过一座还有一座。
如果回头张望,你读过的不过是
刚刚绕过一条河的几个支流,还没有进入主流。
刚刚登上一座小丘,连一道陡崖还没有
翻过。太惨了。譬如你花费十年看到一本书的秘密,
又花费十年才发现,秘密中间还隐藏着更多秘密。
它让你不得不再次回到开始的地方重读。
再一次,你面对的已经不仅是书,是书的宇宙。
这真是相当恐怖的事情。古人说皓首穷经。
你发现首是皓了。但经却无穷。到头来,大概
你只能这样想了,书终会成为你的葬身之地。
埋葬你的不是众多的书,是一本。仅仅一本。
你永远看不到它后面有什么。……原始之书。
夜晚,过墓园……
心血来潮,在山上走着走着,
我决定下山走到小梅沙,然后沿着
海边观光道,穿过华侨墓园返回。
今夜的月亮呈橘红色,很大,
在我到达墓园时刚刚升起。憧憧影影,
各种形状的墓穴在我眼前晃动;鬼谲。
静中仿佛有喧闹。等级制在这里
仍然明确。在我的心里叹息;
灵魂的交流不会发生;有一刻,我想停下来,
看个究竟,终于还是没有。人民有传说,
阴气会细无声潜入身体,令我放弃,
(气,是重要的。特别……)我走得格外有力。
说明,我与他们还隔着一些时间;
时间的光年。就像他们与永恒隔着厚水泥。
他们的亲人在哪里?作为问题
并没有谁关心。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是,
转拐出墓园大门,走最后一段上坡路时,
当我重新见到路上的人,会怎样
看他们;一个女人穿着短裙,一个男人
打着赤膊。被我看成了走动的鬼魂;
死亡,其实就在两里外等待着他们。
选自《江南诗》2020年第1期
以诚实作为基本立场
文/孙文波
随着写作时间的推移,很早以前我就意识到,并越来越明确地相信,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诗歌其实是对自身与所处现实,进行的某种具有认识论意义的解析。这一解析的主旨是通过理解现实生活,以及将之与由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进行语言重组,并将个人的主体性加入其中,从而获得一种具有呈现意味,能够与外部世界对话,带有实体意味的存在样本。而正是因为如此,怎样在具体的写作中落实这一可以被称之为原则性的认识,便成为我在写作中考虑的最多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吧,我的写作基本上是围绕着对这一点的理解展开的。时至今日,我认为大体上做到了对认识到的细节的落实,从而在写作上比较有效地塑造了由此形成的个人风格。对此我的认识是,当一个写诗的人能够通过自身写作呈现出具有辩识度的个人风格时,他的写作才算得上走出了完善自我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工作则是通过更具有穿透力的写作,获得真正地表现出个人品质的新产品。我一直以来都希望自己新作品的生产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出这一点。
这也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非常专注地写作,并有数量比较多的作品产生的原因。以最近四、五年为例,我的作品基本上都保持在每年五十首以上。对于我这样的年龄,每年写如此数量的诗篇应该是很多的了。并且让我感到满意的是,这么多的作品被写出来,还并非仅仅是数量上的收获,在质量上它们也还说得过去。以至于很多更年轻的朋友对此表示,我成为了他们的榜样,一种在写作上由专注而保持了长时期的创造力的榜样。对此我自己亦觉得就专注度而言,我的确可以被称为一种榜样。但是,写作终归不是数量的堆积,而是质量的提升。只不过要获得质量的提升,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坚持对写作本身进行分析。对于我来说,这一点是确切的。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我认为自己基本上做到每一首诗的写作都是在改正中完成的。改正什么呢?改正对以往写下的作品反复审视发现的问题,也就是说,写作对于我来说,发现问题比发扬优点更重要。我最大的希望是,通过对问题的发现,尽可能地使新写出的作品尽量能够以完善的面貌出现。当然,这可以说是一种相当奢侈的愿望。
我就是在这种永远抱着奢侈的愿望的支配下开始写新的诗篇的。对于我来说,这是写作的不满足和写作的新动力。就像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写作中一直希望处理的是怎样在一首关于现实的诗中,引入更为广阔的历史经验,从而使一首诗不单单地成为就事论事的产物,而是真正具有我们称之的“历史感”。对于我来说,所谓的“历史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始终要做到提醒自己,在被称为人类历史的历史序列中,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将自己对之的理解和认识呈现出来,从而使写作出来的作品本身具有与历史与未来对话的可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写作本身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也就是说,写作的另一个意味在于,我们必须将写作导向对怀疑的肯定的方向上去。那么,肯定怀疑的什么呢?对于我来说,这涉及到的是关于诗歌写作的全方位问题,譬如怀疑语言、怀疑语言的可能性,以及怀疑已经掌握的诗歌形式能否完成表达的需要。一句话,在诗歌写作的过程中,用怀疑来求得对新因素、新形式、新的表达方法的发现。
也就是说,没有新因素、新形式、新的表达方法的加入,我们写出的作品其意义和有效性是可以怀疑的,原因在于,新才是诗歌的必要性所在。没有新的出现,诗歌的活力、诗歌在表达现实时让人感受到的力量,都可能无法实现。我一直不希望自己写下的作品,给别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一直在避免诗歌与过去的诗人和同时代的其他诗人雷同、类似这样的情况发生。而接着要往下说的则是,我必须让自己写下的作品,具有独立性。我将这一点看作写作的基本原则。而说到独立性,我想就此多说几句。在当代诗歌写作的场域内部,独立性始终是作为一个问题存在的。因为独立性其实包含了这样几点:一是“独立性”表明在自我认识方面,一个写作者做到了用自己的眼光看问题,二是“独立性”表明写作者在认识语言的功能方面,具有自己的发现,三是“独立性”能够决定写作者最起码站在不受外界的诱惑的角度上,发表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写作作为一种个人行为的基本保证,保证我们在写作中以自我的发现为基本出发点,从而真正地做到所写的每一句诗,都有“诚实”作为保证。
我从来不小看诚实作为保证在写作中的意义,我认为,诚实意味着我们在写作中始终坚持着这样一种原则,即:写出的都是心声——一种经过了人的认识能力处理后的,具有价值观色彩的心声。写到这里,人们可以发现,我回到了一个古老的,关于写作的基本立场上。这一立场似乎在重提写作不过是一种对个人认识世界的关系的目光的再次确定。的确如此。我所有的写作都是基于这一点的,即通过对自我认识的反复书写,表达出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不能在诗歌中反映出我们作为个人的全部文化认识,不能由此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表达自己对生存其间的世界的有效理解,那么写作本身的意义便是“没有意义”。与其那样,还不如不写。这也是说,我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对自我意识的一次肯定。我希望通过这样的肯定向外部表明,只有基于个人的理解我们才会对世界有可靠的认识。我们也才会真正做到写作是属于有话可说后的,符合事物存在规律的行为。并让人们意识到这些话所具有的价值是:诗歌是来自于自我发现的真实声音。而抛开其他的可以不谈,它表明的是:在写作这样的个人劳动中,唯有真实是不可辜负的。
《江南诗》2020年第1期